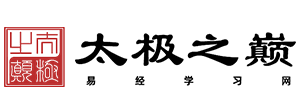【周易上經(jīng)】第2卦-坤卦?坤卦為地(坤下坤上)-[清]李光地《御纂周易折中?卷第一》

坤,元亨,利牝馬之貞,君子有攸往,先迷后得主利,西南得朋,東北喪朋,安貞吉。
本義:--者,偶也,陰之數(shù)也。坤者,順也,陰之性也。注中者,三畫卦之名也,經(jīng)中者,六畫卦之名也。陰之成形,莫大于地,此卦三畫皆偶,故名坤而象地。重之又得坤焉,則是陰之純,順之至,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。“牝馬”,順而健行者。陽先陰后,陽主義,陰主利。“西南”,陰方。“東北”,陽方。安順之為也,“貞”,健之守也,遇此卦者,其占為大亨,而利以順健為正。如有所住,則“先迷后得而主”于利。往西南則“得朋”,往東北則“喪朋”。大抵能安于正則吉也。
程傳:坤,乾之對也,四德同而貞體則異。乾以剛固為貞,坤則柔順而貞。牝馬柔順而健行,故取其象曰“牝馬之貞”。君子所行,柔順而利且貞,合坤德也。陰,從陽者也,待唱而和。陰而無陽,則為迷錯,居后乃得其常也。主利,利萬物則主于坤,生成皆地之功也。臣道亦然。君令臣行,勞于事者,臣之職也。“西南”,陰方。“東北”,陽方。陰必從陽,離喪其朋類,乃能成化育之功,而有“安貞”之“吉”。得其常則安,安于常則貞,是以吉也。
集說:王氏弼曰:至順而后乃亨,故唯利于“牝馬之貞”,“西南”,致養(yǎng)之地,與坤同道者也,故曰“得朋”。“東北”,反“西南”者也,故曰“喪朋”。陰之為物,必離其黨,之于反類,而后獲“安貞吉”。
干氏寶曰:行天者莫若龍,行地者莫若馬,故乾以龍繇,坤以馬象。
孔氏穎達曰:乾坤合體之物,故乾后次坤。地之為體,亦能始生萬物,各得亨通,故云“元亨”,與乾同也。牝?qū)δ禐槿幔试啤袄蝰R之貞”。不云牛而云馬者,牛雖柔順,不能“行地無疆”,無以見坤之德。馬雖比龍為鈍,而亦能遠,象地之廣育也。“先迷后得主利”者,以其至陰,當待唱而后和。凡有所為,若在物之先,即迷惑。若在物之后,即得主利。以陰不可先唱,猶臣不可先君,卑不可先尊故也。
崔氏憬曰:西方坤兌,南方巽離,二方皆陰,與坤同類,故曰“西南得朋”。東方艮震,北方乾坎,二方皆陽,與坤非類,故曰“東北喪朋”。安于承天之正,故言“安貞言”也。
張氏浚曰:君造始,臣代終,人臣立事建業(yè),以有為于下。失朋儕之助,有不能獨勝其任者矣,故“西南”以“得朋”為利,若夫立于本朝,左右天子,茍非絕類忘私,其何以上得君心,合德以治天下哉?然則“得朋”臣之職也,“喪朋”臣之心也,以是心行是職,非曰今日得之明日喪之也。但見君德而莫或有專事擅權之咎,曰“東北喪朋”。
《朱子語類》問:牝馬取其柔順健行,坤順而言健,何也?曰,守得這柔順堅確,故有健象。柔順而不堅確,則亦不足以配乾矣。
項氏安世曰:牝取其順,馬取其行。順者坤之“元”,行者坤之“亨”。“利”者宜此而已,“貞”者終此而已。柔順者多不能終,唯牝馬為能終之。“君子有攸往”,此一句總起下文也。“先迷后得主利”,言利在得主,不利為主也。
楊氏簡曰:君先臣后,夫先妻后。當后而先為迷,迷為失道。君為臣之主,夫為妻之主,后而得主,利莫大焉。
王氏申子曰:乾健行,故為馬。坤亦為馬者,坤乾之配,乾行而坤止,則無以承天之施,而成其化育之功,此所謂柔順之貞,坤之德也。
胡氏一桂曰:“元亨,利牝馬之貞”,已盡坤之全體,“君子”以下,則申占辭也。又曰:彖辭文工所作,“西南得朋”、“東北喪朋”,后天卦位。
俞氏琰曰:坤順乾之健,故其占亦為“元亨”。北地馬群,每十牝隨一牡而行,不入它群,是為“牝馬之貞”。坤道以陰從陽,其貞如牝馬之從牡則利,故曰“利牝馬之貞”。《易》中凡稱“君子”,皆指占者而言。“有攸往”,謂有所行也。坤從乾而行先乎乾,則迷而失道;后乎乾,則得乾為主而利,故曰“君子有攸往,先迷,后得主利”。朋,坤類也。西南坤之本方,兌、離、巽皆坤類,是為“得朋”。出而從乾,則東北震、艮、坎非坤類,是為“喪朋”。君子之出處,隨寓能安,一是皆以貞自持,蓋無往而不吉,故曰“西南得朋,東北喪朋,安貞吉”。
蔡氏清曰:若牡馬則全是健,若牝牛則又全是順。牝馬,順而健者也,要非順外有健也。其健亦是順之健也,故曰“安貞”。坤卦,地道也,妻道、臣道也。不順則專而無成,不健則不能配乾。順而健者,坤之正也。
鄭氏維岳曰:坤配乾者也,坤之德即乾之德,乃柔順以承之而有終耳。有終為健,故曰“利牝馬之貞”。坤道從乾,乾為坤之主,故先則迷,而后則得其所主。“西南得朋”者,率類以從陽,以人事君之道也,“東北喪朋”者,絕類以從陽,渙群朋,亡之道也。此皆陰道之正而能安之,所以得吉也。
喬氏中和曰:坤唯合乾故“得主”,“得主”,故“西南”“東北”,皆利方,“得朋”“喪朋”皆吉事。妻道也,臣道也。妻從夫,臣從君而已矣。
案“后得主”,當以孔子《文言》為據(jù)。蓋坤者,地道、臣道,而乾,其主也。居“先”則無主,故“迷”;居“后”則得其所主矣。“利”字應屬下兩句讀,言在西南則利于得朋,在東北則利于喪朋也,“得朋”“喪朋”正與上文“得主”相對。蓋事主者,惟知有主而已,朋類非所私也。然亦有時而宜于得朋者,西南是坤代乾致役之地,非合眾力不足以濟,于是而得朋,正所以終主之事,是得朋即得主也。唯東方者受命之先,北方者告成之候,稟令歸功,己無私焉,而又何朋類之足云?故必“喪朋”而后“得主”也。為人臣者而知此義,則引類相先,不為阿黨睽孤特立,不為崖異。故易卦之爻有曰“朋盍簪”者,有曰“朋互”者,有曰“以其匯”“以其鄰”者,皆得朋之義也。有曰“朋亡”者,有曰“渙群”者,有曰“絕類上”者,皆喪朋之義也。斯義也,質(zhì)之文王卦圖、孔子《彖傳》而皆合,故自此卦首發(fā)明之,而六十四卦臣道準焉。
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一:坤卦初六
初六,履霜,堅冰至。
本義:六,陰爻之名。陰數(shù)六老而八少,故謂陰爻為六也。“霜”,陰氣所結,盛則水凍而為冰。此爻陰始生于下,其端甚微,而其勢必盛,故其象如“履霜”則知“堅冰”之將“至”也。天陰陽者,造化之本,不能相無;而消長有常,亦非人所能損益也。然陽主生,陰主殺,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。故圣人作《易》,于其不能相無者,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,而無所偏主,至其消長之際,淑慝之分,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。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,其旨深矣。不言其占者,謹微之意,已可見于象中矣。
程傳:陰爻稱六,陰之盛也。八則陽生矣,非純盛也。陰始生于下,至微也。圣人于陰之始生,以其將長則為之戒。陰之始凝而為霜,“履霜”則當知陰漸盛而至“堅冰”矣。猶小人始雖甚散,不可使長,長則至于盛也。
集說:王氏應轔曰:乾初九,《復》也。“潛龍勿用”,即閉關之義。坤初六,《姤》也。“履霜堅冰至”,即女壯之戒。
案:陰陽之義,以在人身者言之,則心之神明,陽也;五官百體,陰也。以人之倫類言之,則君也父也夫也,陽也;臣也子也妻也,陰也。心之神明,以身而運;君父之事,以臣子而行;夫之家,以婦而成。是皆天地之大義,豈可以相無也哉?然心曰大體,五官百骸,則曰小體。君父與夫,謂之三綱而尊;臣子與妻,主于順從而卑。自其大小尊卑之辨,而順逆于此分,善惡于此生,吉兇于此判矣。誠使在人身者,心官為主,而百體從令。在人倫者,君父與夫之道行,而臣子妻妾聽命焉。則陰乃與陽合德者,而何惡于陰哉?唯其耳目四肢,各逞其欲,而不奉夫天官;臣子妾婦,各行其私,而不稟于君父,則陰或至于干陽,而邪始足以害正。在一身則為理欲之交戰(zhàn),而善惡所自起也。在國家則為公私之迭乘,而治亂所由階也。故孔子《文言》,以善惡之積,君父臣子之漸言之,意深切矣。然則所謂陽淑陰慝者,豈陰誠慝哉?順于陽則無慝矣。所謂扶陽抑陰者,豈陰必抑哉?有以化之,斯不必抑之矣。此爻所謂“履霜堅冰至”,其大旨如此。推其源流,則堯舜禹危微之儆,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謹獨之戒,與夫《春秋》名分之防,莫不相為表里。六十四卦言陰陽之際,皆當以是觀之也。
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一:坤卦六二
六二,直方大,不習無不利。
本義:柔順正固,坤之“直”也。賦形有定,坤之“方”也。德合無疆,坤之“大”也。六二柔順而中正,又得坤道之純者,故其德內(nèi)“直”外“方”,而又盛“大”,不待學習而無不利。占者有其德,則其占如是也。
程傳:二陰位,在下,故為坤之主。統(tǒng)言坤道,中正在下,地之道也。以“直、方、大”三者形容其德用,盡地之道矣。由“直、方,大”,故不習而無所不利。“不習”謂其自然,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,在圣人則“從容中道”也。“直方大”,孟子所謂“至大至剛”以直也。在坤體,故以方易剛,猶“貞”加“牝馬”也。言氣則先大,大,氣之體也。于坤則先方直,由“直方,而“大”也。“直、方、大”足以盡地道,在人識之耳。乾坤純體,以位相應。二坤之主,故不取五應,不以君道處五也。乾則二五相應。
集說:王氏通曰:圓者動,方者靜,其見天地之心乎!
孔氏穎達曰:以此爻居中得位,極于地體,故盡極地之義。此因自然之性,以明人事。居在此位,亦當如地之所為。
沈氏該曰:“坤至柔而動也剛”,直也;“至靜而德方”,方也:“含萬物而化光”,大也。坤之道,至簡也,至靜也,承天而行,順物而成,初無假于修習也,是以“不習無不利”也。
《朱子語類》云:坤卦中惟這一爻最純粹。蓋五雖尊位,卻是陽爻,破了體(一當“陣”)了。四重陰而不中,三又不正,唯此爻得中正,所以就這說個“直方大”。此是說坤卦之本體。然而本意卻是教人知道這爻有這個德,不待學習而“無不利”。人占得這個時,若能“直”能“方”能“大”,則亦“不習無不利”,卻不是要發(fā)明坤道。
蔡氏清曰:《乾》九五一爻,當?shù)们回浴Iw乾,孔子以為得天位、行天道、而致太平之占,正是圣人作而萬物睹者,故“時乘六龍以御天”。而致萬國之咸寧者,唯九五一爻足以當之。若《坤》之六二,柔順中正,得坤道之純,是又當?shù)靡蝗ひ病H舫鮿t陰之微,上則陰之極,三則不中且不正,四則不中,五則不正,唯六二之柔順中止,為獨得坤道之純。
又曰:直不專主靜,只是存主處,故曰六二之動。直方可分內(nèi)外,不可專分動靜。
唐氏鶴徵曰:“直”而“大”者,乾之德也。坤無德,以乾之德為德。故乾性直,坤亦未嘗不直;乾體圓,坤則效之以方。德合無疆,則與乾并其大矣。唯以乾之德為德,故“不習”而”無不利”,所謂“坤以簡能”者如此。
案:乾為圓則坤為方,方者坤之德,與圓為對者也,故曰至靜而德方。若直則乾德也,故曰“夫乾其動也直”。大亦乾德也,故曰“大哉乾元”。今六二得坤德之純,方固其質(zhì)也,而始曰“直”終曰“大”者,蓋凡方之物,其始必以“直”為根,其終乃以“大”為極。故數(shù)學有所謂線而體者,非線之直,不能成面之方。因面之方而積之,則能成體之大矣。坤唯以乾之德為德,故因“直”以成“方”,因“方”以成“大”,順天理之自然,而無所增加造設于其間,故曰“不習無不利”。習者重習也,乃增加造設之意。“不習無不利”。即所謂“坤以簡能”者是也。若以不習為無藉于學,則所謂“敬以直內(nèi),義以方外”者,豈無所用其心哉?
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一:坤卦六三
六三,含章可貞,或從王事,無成有終。
本義:六陰三陽,內(nèi)含章美,可貞以守。然居下之上,不終含藏,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,則始雖“無成”,而后必“有終”。爻有此象,故戒占者有此德,則如此占也。
程傳:三居下之上,得位者也。為臣之道,當含晦其章美,有善則歸之于君,乃可常而得正,上無忌惡之心,下得柔順之道也。“可貞”,謂可貞固守之,又可以常久而無悔咎也。或從上之事,不敢當其成功,唯奉事以守其終耳。守職以終其事,臣之道也。
集說:王氏弼曰:三處下卦之極,而不疑于陽,應斯義者也。不為事始,須唱乃應,待命乃發(fā),含美而可正者也,故曰“含章可貞”也。有事則從,不敢為首,故曰“或從王事”也。不為事主,順命而終,故曰“無成有終”也。
楊氏簡曰:無成無終,亦不可也。無成有終,臣之道也。
胡氏炳文曰:陽主進,陰主退。乾九三陽居陽,故曰“乾乾”,主乎進也。坤六四陰居陰,故曰“括囊”,主乎退也。乾九四陽居陰,坤六三陰居陽,故皆曰“或”,進退未定之際也。特其退也,曰“在淵”,曰“含章”,唯進則皆曰“或”,圣人不欲人之急于進也如此。三多兇,故圣人首于乾坤之三爻,其辭獨詳焉。
俞氏琰曰:坤道固宜靜而有守,或有王事,則動而從之弗違也。“無成”,謂持美以歸于君,不居其成功也。“有終”,謂職分居此,則當終其勞也。
蔡氏清曰:六陰三陽,亦有順而健之意,故“無成有終”。亦“先迷后得”,“東北喪朋”,“乃終有慶”之意。
陸氏振奇曰:其不敢專成者,正其代君以終事而不為始也。是即安于“后得主”之貞者與?
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一:坤卦六四
六四,括囊,無咎,無譽。
本義:“括囊”,言結囊口而不出也。“譽”者過實之名,謹密如是,則無咎而亦無譽矣。六四重陰不中,故其象占如此。蓋或事當謹密,或時當隱遁也。
程傳:四居近五之位,而無相得之義,乃上下閉隔之時,其自處以正,危疑之地也。若晦藏其知,如括結囊口而不露,則可得“無咎”。不然則有害也。既晦藏則“無譽”矣。
集說:劉氏牧曰:坤;“其動也辟”,應二之德;“其靜也翕”,應四之位。翕,閉也,是天地否閉之時,賢人乃隱,不可炫其才知也。
俞氏琰曰:咎致罪,譽致疑,唯能謹密如囊口之結括,則“五咎無譽”。
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一:坤卦六五
六五,黃裳,元吉。
本義:黃,中色。裳,下飾。六五以陰居尊,中順之德,充諸內(nèi)而見于外,故其象如此,而其占為大善之吉也。占者德必如是,則其占亦如是矣。《春秋傳》南蒯將叛,筮得此爻,以為大吉,子服惠伯曰;“忠信之事則可,不然必敗。外強內(nèi)溫,忠也;和以率貞,信也,故曰“黃裳元吉”。黃,中之色也;裳,下之飾也;元,善之長也。中不忠,不得其色;下不共,不得其飾;事不善,不得其極。且夫《易》不可以占險,三者有闕,筮雖當,未也。后蒯果敗,此可以見占法矣。
程傳:坤雖臣道,五實君位,故為之戒云“黃裳,元吉”。黃,中色;裳,下服。守中而居下則“元吉”,謂守其分也。元,大而善也。爻象唯言守中居下則元吉,不盡發(fā)其義也。“黃裳”既“元吉”,則居善為天下大兇可知。后之人未達,則此義晦矣,不得不辨也,五,尊位也。在它卦六居五,或為柔順,或為文明,或為暗弱,在坤則為居尊位。陰者臣道也,婦道也。臣居尊位,羿、莽是也,猶可言也。婦居尊位,女媧氏、武氏是也,非常之變,不可言也。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。或疑在《革》湯武之事猶盡言之,獨于此不言,何也?曰:廢興,理之常也;以陰居尊位,非常之變也。
集說:孔氏穎達曰:“黃”是中之色,“裳”是下之飾。坤為臣道,五居尊位,是臣之極貴者也。能以中和居于臣職,故云“黃裳元吉”。元,大也,以其德能如此,故得大吉也。
《朱子語類》云:“黃裳元吉”,不過是說在上之人能盡柔順之道。黃,中色,裳是下體之服。能似這個,則無不吉。這是那居中處下之道。乾之九五,自是剛健的道理。坤之六五,自是柔順的道理。各隨它陰陽,自有一個道理。
項氏安世曰:陰以在下為正,陽以在上為正。故二五皆中,而乾之天德獨以屬五,坤之地道獨以屬二。下非陽之位,故《乾》之九二,為在下而有陽德者。上非陰之位,故《坤》之六五,為在上而秉陰德者。黃者地之色,裳者下之服,文者坤之象,皆屬陰也。
案:《易》中五固尊位,但圣人取象,未嘗卦卦皆以君道言之,雖九五猶然,況六五乎!故《小過》之六五則言“公”,《離》之六五則言“王公”。大概居尊貴之位者,與卦義相當,則發(fā)其所當之義。程子之說,朱子蓋議其非也。
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一:坤卦上六
上六,龍戰(zhàn)于野,其血玄黃。
本義:陰盛之極,至與陽爭,兩敗懼傷,其象如此,占者如是,其兇可知。
程傳:陰從陽者也,然盛極則抗而爭。六既極矣,復進不已則必戰(zhàn),故云“戰(zhàn)于野”。“野”,謂進至于外也。既敵矣,必皆傷,故“其血玄黃”。
集說:孔氏穎達曰:即《說卦》云“戰(zhàn)乎乾”是也,戰(zhàn)于卦外,故曰“于野”,陰陽相傷,故“其血玄黃”。
侯氏行果曰:坤,十月卦也。乾位西北,又當十月。陰窮于亥,窮陰薄陽,所以戰(zhàn)也,故《說卦》云“戰(zhàn)乎乾”是也。
李氏開曰:曰“龍戰(zhàn)”,則是乾來戰(zhàn),不以坤敵乾也。
馮氏椅曰:主龍而言,則知陰不可亢,亢則陽必伐之,戒陰也。以戰(zhàn)而言,則知陰不可長,長則與陽敵矣,戒陽也。
胡氏炳文曰:六爻皆陰,而上卦之上曰龍,有陽也。不言陰與陽戰(zhàn),而曰“龍戰(zhàn)于野”,與《春秋》王師敗績于茅戎,天王狩于河陽,同一書法也。
用六,利永貞。
本義:“用六”,言凡筮得陰爻者,皆用六而不用八,亦通例也。以此卦純陰而居首,故發(fā)之。遇此卦而六爻俱變者,其占如此辭。蓋陰柔不能固守,變而為陽,則能“永貞”矣。故戒占者以“利永貞”,即乾之“利貞”也。自坤而變,故不足于“元亨”云。
程傳:坤之“用六”,猶乾之“用九”,用陰之道也。陰道柔而難常,故“用六之道,利在常永貞固”。
集說:孔氏穎達曰:言坤之所用,用此眾爻之六。坤是柔順,不可純?nèi)幔世凇坝镭憽保坝馈保L也;“貞”,正也。言長能貞正也。
《朱子語類》云:乾吉在“無首”,坤利在“永貞”,這只是說二用變卦。
胡氏炳文曰:坤“安貞”,變而為乾,則為“永貞”。“安”者順而不動,“永”者健而不息。乾變坤。剛而能柔。坤變乾,雖柔必強。陽先于陰,而陽之極不為首。陰小于陽,而陰之極以大終。
顧氏憲成曰:“用九”無首,是以乾入坤。蓋坤者乾之藏也。“用六”“永貞”,是以坤承乾。蓋乾者坤之君也。
何氏楷曰:乾道主元,故曰“乾元用九”。坤道主貞,故言“用六永貞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