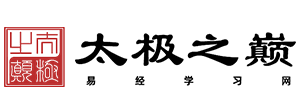一貫-[清]胡煦撰《周易函書?別集?卷八》
一貫
一貫者,內外一如,顯微無間,體用之流通也。無體非用,則不淪於虛;無用非體,則不至於偏而不舉。
聖學原有悟境,亦莫難於悟境。如以為無難,則一貫之傳,何僅兩人?而喟然嘆興者,胡不多覯哉?
宋儒唯程子體用一原,顯微無間,是實從妙悟得也。從前節節次次,俱有障礙,到此忽然打通,全不費力,所以為難。
一貫之說,曾子唯而門人疑,是悟者少而疑者多也。今時粗淺訓詁,便人人信為得解,至窮其所得之解,不過曰一理而貫通萬事。豈謂今人率皆超越門人,上同曾子乎?何悟者之多也!豈謂當時門人盡皆不能作如此解說乎?何悟者之少也!豈謂曾子尚不能作如此解說以曉諭門人乎?何易辭以相質也!若猶未也,政恐後人之能信,不逮門人之能疑遠甚。蓋能疑者猶向此中打點,不肯輕易置去,而能信者遂人人自認為得解,絶不知有妙悟一境矣。
後儒詳於言學,撥去悟境,間有及之者,指為釋家之頓教。至窮其所學,不過格物窮理,道問學盡之矣。果爾,則夫子之告子貢女以予為多學而識其語,非矣。甚矣!是行乎半至之途,而自謂到?者也。
孔、顔之樂,只是道理融通,渾而為一,無逆於心耳。顔子之好,好此者也。若但執博聞強記為學,終墮子貢多識一邊。但走顔子博文一路,恐時習而說之,境界尚未易到,何云孔、顔之樂?蓋孔、顔之樂,即一貫之妙也。
一以貫之,只是道理融通,渾而為一,外無所隔,內無所窒而已。今曰一理而貫通萬事,既有理事之分,又有一萬之別,烏能貫而為一?況用而字一轉,是又將內外前後分作兩截,貫而不一,烏云貫乎?
學聖人者,未易知孔子之一貫,且先識孔、顔之樂;未易知孔、顔之樂,且先學顔子之好;未易知顔子之好,且先學孔子之時習。但能造到悅的時候,便臻於好與樂也不難。然後人之學,求知而已。逮於略觀大意,便謂已解。甚矣,好與樂之難也!
子思曰:率性之謂道。孟子曰:萬物皆備於我。
又曰:仁者,人也。合而言之,道也。
又曰:形色,天性也。此皆內外一貫之妙也。
子思由中和說到位育,孟子好辯章,將欲挽回天時人事,而但曰正人心,此亦天人一貫之妙也。要非孟子不能辨此。
子貢曰:性與天道,不可得聞。然則論語亦有言性者乎?曰:有。一以貫之,天下歸仁是也。性不可言,故止言性中之大用,而曰吾道禮樂刑政,聖人之參贊位育道也;謹言慎行,戒慎恐懼,一身之參贊位育道也。要必有大本存焉,故曰一以貫也。至一而不可言矣,宮牆之美富,一之敦其化原者,不可言也。天下歸仁,一中能貫之妙也。功力可加,在將發已發之際,未發之中,非功之所可至也。故夫子之教回也,教以勿視勿聼,去其外干者,以養其中存者而已。孔子釋乾元,但云萬物資始,其為所資者,不可得而言也。時乘六龍,則能貫之妙;各正性命,保合太和,則已貫之妙也。因性命各正之後,所保者止此太和,故曰一以貫也。今將執一理而貫通萬事之說推之,如但向口頭念過,一與不一,貫與不貫,何待問哉?如克向自己心上體貼一番,先執此一理以周於事,事則拘理以觀事,而實則一事各有一理,已非此一理之所能貫。執一事各有一理之說,則又逐事以分理,不可謂貫之出於一。是此一言,先有語病,其病在理字耳。不知此政夫子之道也。夫子不能添說一語,謂非實由妙悟,不易得解。後來解此者,唯程子體用一原,顯微無間二語耳。天下無二道,率性之謂道,即此道也。推中之所由發,則和為逹道;究和之所由起,則中為大本。是費而能隱,造端夫婦,察乎天地者也。一乎二乎,貫與不貫,蓋可知矣。曾子以忠恕解之,如但將忠認作忠,恕認作恕,何由能貫?乃窮忠字之究竟,原不以人而隔也;窮恕字之原頭,又不以我而塞也。是忠恕亦借來字面,其妙則人已流通於無間而已。第道字所該甚廣,今但就人已最關切處指明之,故遂以為淺言之也。然非博學於文,約之以禮,到底不能得一,又烏得而謂為貫乎?況既添出萬字,萬矣而謂為一乎?自非逹道,未易辨此。
莫問如何能貫,只此一字,可該六經之旨,可括周易之藴,可顯圖書之秘,可逹性命之原。但止逐字分疏,便屬差別。不知此一,何由能貫?不知此一,亦并不是貫。此豈一理字所能明了?理之為言,在逐事逐物條理分疏處見得者也。觀窮理盡性至命之說,則理之一字,止是初地下手工夫耳。
見得無窮盡,故子悅漆雕開;見得無方體,故夫子與曾點。合此六字,方成一貫。方是夫子之道,回兼有之,顔氏之子其庶乎!故不待語以一也。
無窮盡,無方體,渾而一之,方是夫子之道,而開與點各見其一半,故程子謂二子已見大意。
無窮盡者虛也,無方體者靈也。若將虛靈二字打合一片,則杳不可得其解矣。聖人之一,烏可言說乎?
有散錢而無索子,是博而未能約也;有索子而無散錢,是約而未能博也。夫博約二端,是初學者一邊事,以此為一貫則誤矣。若使一屋散錢,用數百丈索子,只這一條索子,便教他擔持不起,何也?博約之見未忘,何由能一?子思說出未發,隨便說出發字,若非中之所有,便是外面襲取來的,何由能發?何由能發而中節?若將中和分作二者,便不解大本逹道流通之故,便不解發而中節之妙,便不知子思於中和之上止用一致字之旨,何由知孔子之一?
顔子去聖人一間,是據三十時說也。然顔子卒時,年止三十二歲。若云三十時,便與聖人之神化相去一間。設顔子而至七十,比諸從心不踰之夫子,不大超越乎?須知夫子三十而立,顔子三十而如有所立,此其相去一間者也。
孟子之性善,即子思率性之謂道。其善也,則發皆中節之旨也。蓋人喜怒哀樂之性,原根於無思無為之天,本皆大中至正,無少偏倚,感以外緣,投之物欲,而汨其本矣。如見美食而悅之,見粗糲而惡之,見章采而悅之,見敝緼而惡之,其初止感於見聞,動於可悅可惡已耳。愈積愈多,愈積愈久,盤根固蒂,觸處發生,罔非惡緣,胥成邪妄,與根心無異。緣其所由,皆外感聞見,留其根蒂者也,故曰非禮勿視,非禮勿聽。視聽不可絶,絶其所由視聽者,故曰克己。不見之色,不聞之聲,絶不入其夢想,未常視聽故也。遺腹之子不夢父,彼於視聽未有所緣耳。見聞之伏而隱,隱而見,其幾危矣,故克己者慎之。人之生也直,
朱子曰:生理本直。理本直三字,只是一箇生字耳。蓋靜專動直者,乾元之亨而利也。乾之直在動處見,人之直正在生處見,以人之資始資生,皆資乾元之動直而始,所以曰率性之謂道。到得在人,雖窮兇極惡,莫不有平旦之氣存焉,中庸所由曰誠者自成也。若罔之生也,幸而免,則所謂不誠無物者也。
夫子之言性與天道,不可得聞。
又曰:朝聞道,夕死可矣。聞也者,不可得聞而聞之者也。聖人之言性、言天、言道,見於四子、六經,蓋亦多矣。今人得其言而解之,便以為聞道者乎?便皆如聖人之所謂可乎?若猶未也,則聞之為說,必有不可解說、不可得聞之妙在其中矣。既曰朝聞,又曰夕死,則必有倏然轉移之一境也。不云數十年之積累,而但取必于一朝,是悟非悟,當自了然。後來學者,不一提掇道字,終日言學,皆未聞道者耳。甚至舉起朝聞夕死之說,便指為佛氏,放下屠刀。噫!宮牆外望之人,其不可與言聖人之美富,亦已久矣。
聖人之道,實有悟境,此境一觸,則萬理皆融,全不費力。今試觀人同此心,人同此知,智者之知,愚者之知,皆無異心也。譬之愚者,一事未達,逢智者解說之,而不覺其豁然,則此一事之明了,即一事之悟境也。夫未明之先,與既明之後,其境在倏然之內,忽而改觀,人之悟境,亦復如是,然止可為知者道耳。又如學者讀書,因一二字未解其義,遂使全章皆不得其旨,若得明者解之,不覺其豁然通透矣,此一字之明了,即通章之妙悟也。聖人之道,天地之大,萬物之廣,身心性命之精微,天下國家之遠大,罄天地所有之書,解說所不能盡,茲欲於一心之中,窮其原而竟其委,非由妙悟,曷克幾此?如但執為放下屠刀之說,而不知聖學實有悟境,則是四書六經以外之學,非四書六經以內之學也。
論語為聖人傳道之書,精及於一貫之微,粗及於飲食、衣服、語言、起居之細,何非道之散見?然非有論語顯易明白,可以探本窮源,則周易之旨,終不可得而逹也。朝聞道者,是由博返約,貫萬於一之大幾也。即顔子之高堅前後,如有所立,參、賜一以貫之之候也。故下曰夕死可矣。
陽明謂一如樹之根本,貫如樹之枝葉,未種根本,有何枝葉可發?此言亦未當。一,本也;萬,枝葉也。貫則其中之精脈,徹上徹下,而不少欠缺者也。故此一句,唯貫字最妙,指出一字,直提掇源頭耳。其文原未及萬,故不可以萬字對此一字,萬字小對一字。不過聖人但曰貫之,不曰貫萬,如云只是這箇充塞於天地間耳。
孔、孟之道,實非一蹴可至,深積力久,由博反約,實有穎悟存焉。只為此等境界,非粗淺者所能遽達,故一貫之旨,唯曾子、子貢始得而聞。後之儒者,止據一人之眇見,存為論說,拘而守之,不肯濶開一步。其於陸、王,則指為頓悟,指為放下屠刀。夫聖門而無悟境,則一貫之理,亦何人不可解說?當不獨參、賜兩人,而朝聞夕死之說,亦聖人之贅語矣。且但如後儒所解,則人誰不知?然而人皆可以夕死乎?若猶未也,則室中之美富,恐非宮牆外望者所能測也。
夫子之語曾子曰:吾道一以貫之。曾子曰:唯。解之者悉知其為曾子之悟,不知後儒何忽謂悟為頓教?然則曾子之在聖門,亦止可為頓教乎?據後儒之意,不過謂人之於道,當以積學為要耳,所以有深積力久之說。然則陸子之與陽明,竟是不曾讀書,字即不識,義即可解者乎?且但以積學為主,吾不知學而不思,又當為何如人也?況自周秦迄今,其間博物洽聞者,蓋亦不乏,果盡為知道者乎?果爾,則聖人之門,身通六藝者,蓋亦有人,何未聞孔子之以一貫告也?且孔子之語子貢也,曰: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?則多學而識,其不足以盡聖道也,亦已審矣。孔子而後,幸有子靜、陽明,其超悟逾量,其事功卓絶逾量,曾未有纎毫與聖教相違,顧乃不滿於後儒之心。即其不滿此兩人者,究其讀書之精,超悟之妙,行事之當,又未能盡逾此兩人,亦見其妄矣。當知學悟兩途,皆聖人所屬望於人者,特學易而悟難耳。學且不悟者,比比皆然;學而悟,則絶少矣。子思之言曰:尊德性而道問學,致廣大而盡精微。尊德性而不致於廣大,道學問而不盡其精微,恐皆為半至之學也。行半至之途,幸毋輕詆升堂入室者也。
周易者,博文約禮之書也。其天地人物,精粗巨細,罔不具載,則文之博也。故君子之格物,當由周易而始。周易之物不格,何物之能格乎?合四聖之易而論之,爻歸於卦,卦歸於圖,則禮之約也。伏羲由外之六十四象而歸於兩儀,由兩儀而歸於太極,是顯微闡幽之妙也,則禮之約也。文王之元亨利貞,七日來復,維心亨,則禮之約也。周公於始成之爻,命之為初,而乾坤兩卦,特添用九、用六兩節,則禮之約也。至於孔子乾坤彖傳、文言,以及窮理、盡性、至命、繼善、成性、顯仁、藏用諸傳,皆禮之約也。不博固無以為約,徒博亦必不能約。故必兼是二者,然後可幾聖人之一貫。博文非一家之文,徒資腐陳之糟粕,而人人咂其旨甘,究復何味?約禮非拘固之理,未悉衆妙之本原,而空空存此靜寂,亦復何貫?
子思、孟子皆孔子一脈相傳,深於一貫者也,故克與顔、曾二子并稱大賢,列為四配。子思曰:天命之謂性,率性之謂道。此是一貫話頭,只一性字便該之矣。天則性中最初之命賦,道則性中推行之作用也。子貢之言性也,亦兼言天道,天所以原其始,道所以究其終也。此子思之一貫也。梁襄王問曰:天下烏乎定?孟子曰:定於一。孰能一之?曰: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只此不嗜殺三字,各正之太和原是如此,長善之仁便是如此,仁民愛物推恩之廣全是如此,此所由斷斷乎謂性為善也。
又曰:仁也者,人也,合而言之,道也。
又曰:形色,天性也,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。
又曰:萬物皆備於我矣。此孟子之一貫也。悟也者,倏然之事,非積累之事也。夫積累云者,窮理格物之學,求適乎悟之一途者也。此但搜剔字義,求明章句而已。然非漸而積之,則事物之理不能畢逹。逮於窮理而理明,格物而物格,有以探本歸原,則倏然之境矣。譬如今人作文,一題入手,若有些子不能透闢,則或終歲終月不能置筆。茍得旁人一發明之,或因自心之觸悟,而心地倏然澄徹,此非暫時驟通之事乎?聖人之學,窮理格物者,在平日則積累之事也;偶然感觸者,在當機則倏然之事也。夫子以一貫語曾子,而曾子曰唯,非其積累既深,轉為倏然之機乎?若顔子之不違,則無所容其悟矣,所由高於曾子一等也。如僅執窮理格物為是,頓悟為非,則行乎其途,而未逹地頭者耳。然而一貫之妙,非其人不易領會,所由非頓而是漸歟?
一而不一,則不淪於拘墟;貫而有所以貫,則不病於紛擾。
聖與儒何分?孔子之於周易也,如乾元用九,乃見天則,復見天地之心,易簡而天下之理得,窮理盡性以至於命,易冒天下之道,成性存存,道義之門,至精至變至神,皆說向精深沉細一邊。後儒教人,但教以窮理格物,道問學,第說向粗淺顯易一邊,是為學者言之。可知精深沉細一邊,後儒尚未言及。
一以貫之與天下歸仁,止是一義。仁即所貫之一,天下歸則能貫之妙也,不待既貫乃始知之也。
聖人之學,無過知行二端。其知難而行易者,必事事察識詳明,然後能委曲周詳而無誤也;不然,則疑畏而不能前矣。其知易而行難者,必事事身親歷過,然後能窮理而至命也;不然,則虛懸而無所得矣。故人之有德者謂之德行,謂有行而後能得之於已。聖人之道,貫於參贊位育一邊,乃始謂之為道,是即德行之充也。一貫之說,參、賜雖同而實異。曾子由力行而入,故一點便知。子貢由多識而入,其行尚在後面,故有不欲勿加之說。夫子曰:非爾所及。
元亨利貞,乾之一貫也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,利用安身以崇德也,人之一貫也。天地絪緼,萬物化醇,男女搆精,萬物化生,天之一貫也。
學人終身馳騖於名利塲中,聞人所聞,充口便言性學,此執樵夫之斧柯,而妄擬海舟之篷槳也。靜中之妙,不曾體貼一月半月,執古人片言隻字,而胸無確見,皆隔膜者耳。
一之云者,無可分別之名也。貫之云者,是有可分別,而仍無可分別之名也。至曾子之告門人,是專說人已相接之事,宜乎確有分別,而卻專為恕字留神。何也?謂人知忠為盡己之事,恕為及人之事,判然各別,而不知恕之及於人也,皆忠內事也,故曰忠恕而已矣。如云恕亦莫非忠耳,觀孔子之告樊遲,以忠為與人之事,則恕可知矣。如此,則朱子盡己、推己二解,亦有半是半非。其曰盡者亦己,推者亦己,是也;其於忠則曰盡,於恕則曰推,非也。當知所推之己,仍然是自盡之己也。
曾子告門人,舉出忠恕原因。門人皆知忠恕本是兩事,卻要使他知其中一脈相通之故。如云:人知忠為自己一身之事,第及人而不如其為己,則不可以為忠。人知恕為及人之事,為人而不能實盡其在己者,則不可以為恕。故及人之事,皆自盡之事,此方是一貫之旨。天下歸仁,是顔子之一貫。中也者,天下之大本,是子思之一貫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,是子貢之一貫。仁也者,人也,合而言之,道也,是孟子之一貫。
曹月川曰:一是仁之體,貫是仁之用。
薛敬軒曰:夫子所謂一,即統體之太極也。所謂貫,即各具之太極也。
【煦】按:此解便與以仁分體用者迥別,天下何嘗無解人,可知敬軒造道之深。